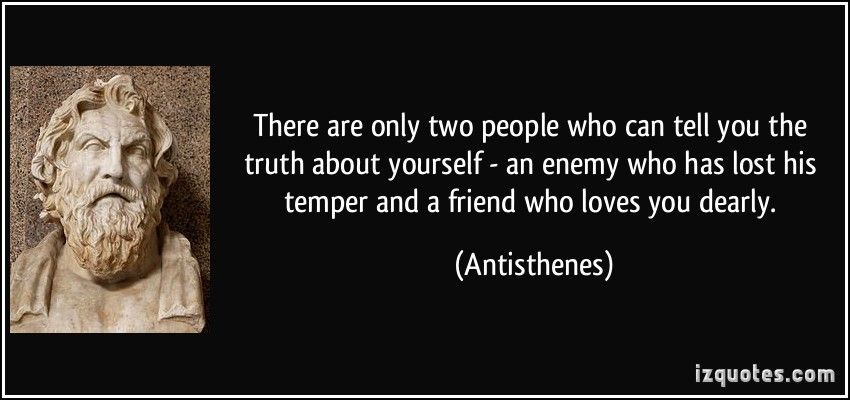誰搬走了我們的半塊芝士: [第二章]第七十集:會告訴你真相的,只有兩種人
(陳錦波部份)
一張開眼,第一眼見到的,是一大片木製的天花板,我坐起來,摸一摸自已的臉,那副在溥儀四的價值八千元的眼鏡依然在臉上,好讓我可以看清楚自己正身處在什麼地方。
一眼看看周圍,我正在一個一足一千呎的空間裡,這裡只而兩種東西,一是大大小小的酒櫃,二就是被我所坐著,全倉共有幾十個的啤酒桶。
我拿出褲袋裡的IPhone,已經是十一月十日的早上十時,闖入3K黨總部是十一月九號夜晚的事,看來我又不知不覺訓了超過二十四小時。已經是第二次睡得這麼久,發生這樣的事只有兩個可能性,有可能因為時差問題以致我內分泌出現問題,所以訓極都唔夠,亦有可能是我原來身懷古怪絕症。
答案我話你知,肯定係第一個!我同你講一個前幾日先玩完3P既人有絕症,你信唔信啊!?緊係無可能啦!
但其實都唔係無可能既,不過我話無就無啦,你唔好同我拗喇,收皮啦。
如果你問我,點解而家會係個貨倉入面,我可以話你知,應該係老酒保所做既好事。不過確實既情況係點我唔太清楚,但我可以同你講返,果一槍之後究竟發生左乜野事。
「砰!」
當時,隨著一記的槍聲,首領話都未說完,本該繼續說話的頭就消失了。
其實說是消失了好像有點不貼切,正確點說,他不是成個頭無鳩左,其實重剩返個下巴。
在爆頭的一瞬間,我身上並沒有沾上半滴血,但兩秒後我被他傷口位置所噴出的血搞到成身都係。
究竟邊撚個打爆佢個頭!?唔通係樓梯果邊有人上左黎開槍!?一望過去,鬼影都無隻。
那麼是遠方的狙擊手所下的毒手嗎?我左顧右盼,觀察每一個扁平的窗……都是完好無缺的……連半個洞都沒有。
既然兩個最大的可能性都不是,那是誰殺了首領?老酒保?被我綁住,正一臉驚慌的polo恤白鬼?還是在一角躺著,被五花大綁的盧卡斯?
望著幾個嫌疑犯,我皺一皺眉,看來案情並不是這麼單純……
不過,我都唔知個死白鬼有無病,所以首先要趕快抹一抹身上的血。我一邊脫下外套,一邊思考一件事,就是在這間房間有誰持有著足以打爆人頭的強大火力?
實在怎都想不透,難道那白鬼的頭上早已裝著炸彈,只要講錯野就會爆炸?這種情節我在電影見過不少。
為了脫下外套,我必須先放下手上的短獵槍……望一望才發現,槍管正冒著硝煙……
點解會咁樣?原來兇手就係我?我愕然,望一望支槍,再望一望那具無頭屍……
屌你老母!!我殺左人!?
我殺鳩左3K黨既首領!?
點解會咁嫁!?我完全無殺佢既意思嫁喎!!點解佢會無啦啦死左嫁!?係唔係支槍會無啦啦走火!?
屌!我唔記得喇!!但我真係無心殺佢嫁!!
我抱著頭,正苦惱著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意外的時候。
「喂,越南人,在事情鬧大之前要走了。(英語)」是老酒保的聲音。
回頭望過來,發現他已經像托著死屍一樣,用手臂固定著盧卡斯一手一腳,四平八穩地站著,我見到盧卡斯口腫面腫,發紫的左前臂斷到好似多左個關節咁,而且毫無生氣,都唔知會唔駁唔駁得返。
正當我望得呆了的時候,老酒保咬著煙叮囑我:
「記得帶走你的外套,我們現在就要出發離開。(英語)」
望著首領的無頭屍,我面都青埋,全身都震哂,不知不覺地吐出一句:「But……」
「But?But什麼?你的目的都達成了,還想留在這裡做什麼?想跟屍體繼續傾計嗎?(英語)」
我搖搖頭,拿起外套與短獵槍還有吧枱上的雙槍,就趕緊跟在老酒保後面,瞬速離開3K黨的總部大屋。
回頭望一望大屋,我真的沒想到今次的事件會以這個方式完結……
上到傻豹號,我的記憶就開始模糊,只記得當時我和盧卡斯被丟到後座,由老酒保駕車載走我們。
「我欠你們這些越南人的,一生都還不完。(英語)」
這是我記憶中聽到老酒保所說的最後一句說話,之後發生了什麼事,我們被載到哪裡去,我則連半點印象都沒有。
失去意識期間,我沒有做夢,醒來的時候,已經直接回到現實。然後,一起來我就發現自己的身處在一間貨倉裡,正躺在幾大桶啤酒上面,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。
係我出返去依個貨倉之前,有件事我想同你地講。
你知唔知道?做人只要講左第一個大話,好多野都返唔到轉頭,如果一日唔認衰,你就注定要永遠背負著更多既謊言走落去。
其實來到現在這個時間,我已經受夠了,唔想為左一次吹牛吹大左搞到要吹更多既牛彌補,咁做人會好辛苦,所以我決定向你地坦白。
我以前確實係黑社會,不過事實上大部份時間我都係跟緊雄哥,而我只係佢五條頭馬其中一條。我出冊後兩年,雄哥都未做到坐館就已經比人碌斷腳坐監,見到佢既下場,我就開始行返正行,係M記搵左份西工做住先,做下做下,不知不覺就做鳩到而家。
我最多只可以話行過古惑,但講真,旺角水房六八九幾時輪到我做啊!?何況做得坐館既話,我重洗做M記!?醒D啦!戇鳩仔!人講你就真係信啊?
而我坐監既原因,的確係因為殺左人,但因為當時有個幾犀利既律師幫我打依場官司,所以罪狀唔係蓄意謀殺,而係誤殺。
我在香港的個人身份紀錄上,的確是一個殺過人,坐過監的惡人,不過在這個時空的真實歷史上,殺果個人既唔係我,而係雄哥。
我當時只係捱義氣幫佢頂罪,所以雄哥先會幫我請個好律師。
所以嚴格黎講,直到琴晚開槍既一瞬間為止,我都係一個清清白白,無殺過人既良好人類。
我之前都講過,而家依個世界,都係由經我把口而誕生,作為聽眾,你無選擇既餘地,我講乜,你就要信乜,其實真係非常被動。
但我以人格尊嚴擔保,除左以上果堆野,你地睇到既佔九成以上都係真正既事實。
所以你地要原諒我果份不足一成既錯誤。
其實阿權無死。
佢唔係復活左,定係變成左僵屍,又或者係共濟會的最終頭目,或是一個超能力者。
事實上,我根本無殺到佢。
當日在骨場門口,我所遇到的阿權臉上並無失落之情,反之,他當時正春光滿面。
對於這個偶遇,他非常驚喜,在我提及廠妹之事前,已經被拉到附近一間小菜館食宵夜。
當時我心諗:
「好啊,食飽先都好,你又可以做隻飽鬼,我又可以更加有力咁扑鳩死你,而且夜d行動對我更有利,WinWin雙贏,緊係好啦。」
於是我們去到目標的小菜館,一坐低,阿權居然話今餐佢請,重叫到成枱都係餸,唔知佢係想用地溝油毒死我,定係作為生物的直覺告訴他等等要死,所以連忙食返餐好。
望著成枱餸,香噴噴,理得佢地溝油定萬年油,反正咁多年都食唔少,唔鳩理鳥!
係啊!無錯啊!其實我們吃地溝油真的已經吃了好多年,只是一直不知道罷了。大陸佬為賺錢可以去到好盡,因為大陸係一個有錢就可以為所欲為既地方,只要有錢就可以做皇帝。
所以無論去到邊,大陸佬都總係擺起一副皇帝款,雖然會痞係條街,雖然會隨地吐痰屙屎,雖然會亂掉垃圾,雖然依然會搶奶粉……但他們的自我感覺上都是皇帝,其實都岩既,做得皇帝既,根本就唔鳩洗理你地d賤民既感受。
大陸有地溝油,腎石奶粉,頭髮豉油,共產黨等等的人禍。
但我們香港也不輸蝕!吸血鬼地產商同業主,落盡全力官商勾結既賣港政府,不屈不撓比豬更蠢的愚民,其實香港都好有自己既特色嫁!屌你老母!
其實如果唔係班吸血鬼一日到黑乜都唔洗做,繞埋雙手䟴䟴腳加租,賣港政府又官商勾結,笑騎騎唔做野,加上一大班度縮數賺到盡既杏加橙老細,同埋班殺到埋身都重當無事發生,日日準時反工,唔準時放工,返屋企開開心心睇TVB,戇鳩鳩既愚民……
香港人其實真係未必洗食地溝油嫁。
講撚到尾咪又係犯鳩賤!
食飯時,阿權清醒的時候,我們的對話離不開都是性器官,性器官與性器官,扑野,叫雞,揼骨,仁K……
我想,阿權的身邊,大半生都環繞著這些東西,多年來,他無悔無怨,還樂在其中,但我卻不禁為他而感到悲哀,一個人的一生就只有射精與M記,我都唔知應唔應該將d咁既核突野稱作人生。
不過想一想,我的人生,又何嘗不是這樣?
果晚吃完一大堆地溝油小炒,我同阿權已經喝了數不清那麼多支大青島,雖然他已經醉到成坺屎咁,但我酒醉重有三分醒,所以殺死阿權的計劃依然繼續進行。
阿權醉酒過後,雖然滿咀都繼續是性器官,不過,卻比平時多了一份感性,這讓他在我面前漏口講出與小紅扑野扑到要換床單的事,闖了大禍,今次卻救了自己一命。
我用他銀包裡的錢找數後,便拖行這個爛醉如泥的大男人行走指定的路線,去到我早就準備好的那間單位。
沿途他一直胡言亂語,又問73號小巨肺去左邊,點解咁耐都未黎,忽然又唱海闊天空,為免惹人注目,我將褲袋袋住果幾舊呻過鼻涕既廁紙一野塞哂入佢個口,好讓他安靜一下。
一路上都無遇上任何人,我們就這樣順利到達這個經我準備了多年的單位。
在事實上,我沒有一入屋就用壘球棍打爆佢個頭,因為我當然正非常吃力地拉佢入屋,除非有兩個我,否則我根本不可能做得到這種事。
見佢醉到成條死屍咁撚樣,我將他掉到地面早已準備好的膠布上,然後洗了個臉,涼一陣冷氣,才開電視,拿起壘球棍,對準佢個頭,度好位準備一棍毆落去。
但睇到佢訓到好似死左咁,乜野反應都好,感覺上就好似姦屍一樣(我必須澄清依個只係比喻,我完全無雞姦佢既意思),就算毆落去都無乜癮。
玩得依樣野,就緊係要對方都比反應先過癮嫁啦!
反正電視開得好大聲,我唔怕佢叫救命或者發神經,於是就將他口入面的廁紙取走,好讓他能說句話,講句遺言我才毆落去。
我拍拍他的臉,單刀直入地問:
「喂,阿權,你係唔係屌過小紅啊?」
我已準備好,當他一答:
「啊……?係啊,波叔,小紅個西又窄又多水……」就一棍毆爆佢個頭。
然後他張開眼,戇鳩鳩地望住天花板,望望我,再說:
「波叔,你知唔知啊,我做左咁耐人,你對我就最撚好嫁喇!我話你聽,你對我,重好鳩過我老豆對我啊!」
「其實我記得嫁,我之前漏口同你講錯野,話我屌過阿嫂啊嘛!你知唔知啊?我之後驚撚左成半年,驚你會隊冧我啊?但我諗過,如果你真係要隊冧我既話……我都無辦法……會認命嫁喇……鬼叫自己仆街衰咸濕……」
「但你大人有大量,之後居然重對我愈黎愈好……我真係鬆一口氣之餘,重好撚感動啊……所以……之後阿嫂搵鳩過我好多次,我都無So佢……」
「因為我真係好撚對你唔住啊!」
望住他流到成面眼淚,口水鼻涕流到落件衫,我沉默地站起來,走到一張小椅子上,用了整整一小時思考自己的人生。
期間阿權又講幾次對唔住,然後又憑空屌鳩D M記兼職仔,唱多兩首歌……又開始繼續訓。
我就一直繼續坐,無焦點地望著冷氣機。剛剛阿權的話是酒醉下所說的真心話,還是根本清醒,所有都是求存所說的謊言?做人做左咁多年,真醉定扮醉,我一清二楚。
其實件事都過左咁耐,阿權咁耐以黎都好內疚,何況小紅多年都唔止同阿權做錯事……或者溝得依條女,我應該早就預左會遇到依d事……
最後我問自己,做人做左人咁耐,有幾多人好似阿權咁,係真心尊敬我?
應該就只有阿權一個……
講真,我又點可以殺死世上唯一一個真心尊敬我既人?
這就是我的答案。
就這樣,我帶走阿權離開那本該是屠場的單位,將他丟到一間賓館後,已經天光了,在附近吃過港式早餐後,我就回香港。
雖然殺阿權的計劃取消,但因為我已經買鳩左機票,而且做大事的理想還是沒有變,所以坐飛機到芝加哥的魚柳包之旅還是必須繼續進行。
要問我為什麼要講出真相的話,我只可以說,一個大話,確可以令我威一世,但現在真的殺了人,加上老酒保的故事,讓我知道,自己根本從來無威過,死頂落去係自己攞黎柒。
過去,我同所有男人一樣,衰係面子上,為左保住自己既型像,我將自己愈吹愈大,最後收唔到科,好多野都要死衝,最後我已經趕唔上吹出黎既自己既步伐,我好清楚,繼續衝落去,就只有一個結局等緊我,就係死……
所以,與其將功積建立在從不屬於自己的謊言之上,去扮演一個自己作出黎既角色,不如腳踏實地做返自己,反而更有存在的感覺。
我有信心,而家既陳錦波更有能力幹一番大事!